-
窥探万物运转的秘密,用侦探的方式创作故事|大卫·麦考利专访
潜之龙 / 2024-09-22 17:13 发布
大卫并不是凭借《万物运转的秘密》获得凯迪克奖的。1974年,放弃建筑行业,开始画建筑相关的绘本的他凭借首部作品《大教堂》(Cathedral)获得了凯迪克银奖;1978年,他的《城堡》(Castle)再度获得凯迪克银奖;而1991年,大卫所创作的极具实验性的故事绘本《黑与白》(Black and White)为他夺得了凯迪克金奖。

大卫·麦考利。
《黑与白》是大卫对绘本所能承载的故事形式的尝试——他将一个对开分成四格,分别讲述四个看似无关又有丝丝缕缕关联的奇幻故事。在《黑与白》的凯迪克金奖获奖感言中,大卫说:“我一直鼓励人们问自己:为什么一切是它们看起来的样子。在罗得岛设计学院,我通过教绘画来鼓励提问;在我的书中,我通过建造建筑、大脑,还有解释机器的运转来鼓励人们提问……在《黑与白》中,我的意图是一样的,不过这次的主题是‘书’……这是一本关于关联的书——图画之间的关联,还有文字和图画之间的关联。”

《黑与白》内页,也是书中四个故事的名称页。
一位成功的科普图画书创作者,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建筑学出身的大卫,又是怎样系统地学习物理学、人体科学等复杂的知识,创作出专业又视角独到的科普书?也许这次采访或多或少给出了这些问题的一种回答。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向大卫·麦考利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何创作一本好的科普书?大卫这样回答道:“要创造一本有价值、震撼人心的书,需要运用想象力,因为有许多条迥异的道路通往同一个主题。不过,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决心、耐心、关怀和人情味——这可以通过一个小幽默、一个大惊喜,甚至一次短暂的混乱(它会被某种有意义的抉择战胜)来展现。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投机取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不是心怀真正的热忱,就找不到通向非凡成功的道路。”
因为“亟须找点乐子”,
他创作出凯迪克金奖作品
新京报小童书:很多研究者都指出,《黑与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发掘了图画书的更多潜能,也改变了人们看待图画书的方式。对于一部绘本来说,“黑与白”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也有一些抽象。请问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呢?黑和白是对故事意指的隐喻吗?
大卫·麦考利:对这个问题,我能想到几个答案。首先,我记忆中从父母那里听来的第一个笑话是:“鸡为什么会过马路?”官方答案是:“因为要到马路对面去。”我在出版于《万物运转的秘密》之前的《母鸡为什么过马路》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本书实际是在《万物运转的秘密》创作中途迅速完成的,因为我需要在绘制那些机械图的间隙喘口气)。

《黑与白》,[美] 大卫·麦考利 著,漆仰平 译,洛克博克 出品,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3月
我记忆中第二个笑话是:“什么东西又白又黑,而且从头到尾都是红色的(原文为:What is black and white and red (read) all over。red谐音read,意味着从头到尾都能读)。”答案是——报纸。我觉得这个笑话又好玩又聪明。我决定用“黑与白”这个标题来暗示,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应该被仔细阅读,任何细节都不能忽略。我认为这个题目也是对书中运用报纸这一意象的提示。由于书里出现了火车蒸汽和报纸做成的衣服,画面的艺术风格变得越来越黑白化。
《母鸡为什么过马路》和《黑与白》是一种媒介,我在连续绘制了15年不能有半点废话的科普书后,试图从它们那儿获得一点儿乐趣。

《母鸡为什么过马路》,[美] 大卫·麦考利 著,兆新 译,耕林童书馆 出品,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12月
新京报小童书:《黑与白》是一部突破了普通读者阅读经验的作品,读者可能会在刚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感到困惑,甚至放弃。你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具有挑战性的作品呢?
大卫·麦考利: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能创作出吸引我、挑战我并最终带给我快乐的作品,它很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吸引那些与我相像而不是迥异的读者。我想用这本书挑战自己,不过是将其作为拼图游戏,而非艰深的智力训练。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很简单:我能描述四段不同的旅程,并最终让它们合为一吗?这足以支撑一本书的创作吗?
大约从1980年开始,我就一直在玩味旅行的想法。我觉得我就是想去旅游,但那时不太现实,所以我不得不在我的写生簿上铺展我的旅程。
新京报小童书:我们查到一些背景资料,据说在《黑与白》之前,你一直有创作一部旅行题材绘本的想法,这个想法后来成为《黑与白》四个故事其中之一的《幻影》的雏形。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你是怎么由此联想到其他三个故事的呢?
大卫·麦考利:我在邮件里附上了《万物运转的秘密》的四页草图。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由于只工作不玩耍,我研究力学和物理学时一直分心。事实上,我亟须找点乐子,被困在机械世界的时候尤其如此。

大卫·麦考利在创作《万物运转的秘密》时期的草图,其中藏着《黑与白》中的人物(受访者提供)。
就构思这四个故事而言,我只是调动了自己的回忆。我一直喜欢蒸汽机和它们的烟雾的气味。我最大的乐趣是在车站等车或站在横跨铁路的人行天桥上。我也喜欢乘坐火车。我最爱的利用报纸的方式——除了阅读,就是拿它们包裹从地道小店买来的炸鱼和薯条。那些美食总是用某种白纸包着,外面再卷一层报纸。这是美味至极的废物利用。
我画的奶牛就是用来摆玩图案,并构建画面的。强盗呢,给了我另一个游戏机会来画一个穿着黑与白衣服的人。
把所有零散的图片钉在墙上,
用一种侦探的方式来创作
新京报小童书:我们注意到,在呈现书中四个故事时,你特意运用了四种迥然不同的视觉风格。你是如何确定这些风格的呢?此外,你如何想到把四个故事放到同一个页面来呈现呢?
大卫·麦考利:我想强调的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其独立性,所以只有当我在结尾剥去色彩的矫饰,读者才会开始看到其中的联系。
选择不同的风格是为了尽可能让四个故事看起来不同。而将每个故事的画面同时展现在一个跨页上,则进一步强调了差异,让读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把所有草图都钉在了墙上,并不停地移动它们,尝试不同的故事排布,整本书的设置就是从这逐渐演变而来的。我总是把我的画钉在墙上,看它们如何一起运作,故事的序列如何流动。在开始创作《母鸡为什么过马路》之前,我从没尝试运用这种方法。(我的早期创作更为简单。)你总会对碎片如何组合产生一些想法,但是当你把碎片贴满一面墙,你将会头一次注意到这么多的细节。从某些方面来说,整个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力图找出该删减什么、省略什么。我的草稿数量总是远远超过实际使用的画面数量。
新京报小童书:《黑与白》中四个画面之间总是存在着种种微妙的联系,推动着彼此的发展,此前从未有作者在图画书中进行类似的尝试。请问你在创作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呢?是如何解决的?
大卫·麦考利: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我知道困难往往是最美好的部分。这就是挑战,也是我用一大堆大头针把草稿扎在墙壁上的最佳理由。如果你没有真的确信或者认为自己真的确信,就不要敲定。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可能有点令人挫败,但它大体是绝对稳妥的。
只有当我在墙上确定了一个可行的序列,我才开始看到各种连接的可能性。例如,火车故事中的云(此处“云”为受访者口误,在书中为“雪花”)看起来像另一个故事中的撕碎的信件。

《黑与白》内文图。
新京报小童书:你是如何想到打破四个故事的框架,让不同故事里的人物和事件渗透到其他故事中的呢?
大卫·麦考利:当我把所有零散的图片钉在墙上时,我很容易就能发现其中的欠缺——某些地方可能需要一个草图来过渡——所以我会把这个草图画出来,然后再钉起来。或者,我会注意到一些片段(它们当真都是片段,都是些扫描图、照片拷贝的碎片)可以有更好的安排,因此我把它们剪下来或撕下来,重新放置。转变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草图转换成另一个草图,一个“故事”代入了另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
新京报小童书:当读者耐心读完四个故事之后,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几个故事是互为因果的。不过,这些故事之中也有一些供读者自由解读的留白。你认为读者应该如何阅读这个故事——是像侦探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推理出你头脑中既定的故事,还是发挥自己的想象、用自己的方式去补全整个故事?对于《黑与白》,谁更有解说权,是作者,还是读者?
大卫·麦考利:不管是怎样的留白,它们都发生了。它们之所以被保留下来,要么是因为它们参与了创作,要么是因为它们勾连起了两幅插图,从而将两个或更多的故事连缀在一起。
我非常同情那些试图弄清楚我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可怜读者。多半时间里,就连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我倾向于认为,这本书的读者会注意到那些令人吃惊的联系,然后他们会发现翻回故事的开头,尝试弄清自己错过了什么。我猜这就是一种侦探的工作方式。我非常确信,无论是在我的书里,还是其他书中,仔细观察艺术作品是必须的和值得的。
我从不认为这本书的故事可以在任何层面上改变世界,不过我觉得我创造了一段旅程,它可以给读者带来欢乐和满足,这种感受甚至可以从第一次阅读绵延至第二十五次阅读。
新京报小童书:有读者根据第二个故事《现代父母》中长着强盗眼罩花纹的狗、玩具火车、电视里的通缉令、最后出现的站台拼图,推测另外三个故事都出自这个故事主角的想象。是这样的吗?你会如何解读这四个故事之间的关系呢?
大卫·麦考利:它们彼此的关系可谓异想天开,但与此同时,它们之所以能够汇聚在一起,是因为背后有着共同的逻辑。我认为,正因如此满足感才油然而生。不仅我已将其厘清,读者也必须将其厘清。

《黑与白》版权页的彩蛋,第二个故事中的孩子拿起了第三个故事中的车站布景。
通过提出问题来分解事物,
直到有能力“重建”我的主题
新京报小童书:你曾说过,童年时就对手工和绘画非常感兴趣。我听说,你那时还很喜欢制作机械模型,绘制各种机械图。你小时候想象过成为一位绘本作家及插画师吗?在许多创作中,你都展现过扎实的绘画功力,请问你的绘画技巧是自学的,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呢?
大卫·麦考利:作为一个孩子,我没有足够远大的想象力来把创作图画书当做梦想。直到大学毕业,我才对图画书有了真正的了解。当时我正试图弄清自己究竟想做什么,而一些有孩子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他们与孩子共读的书籍。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考虑创作图画书的可能性,而且我越想就越欲罢不能。从小到大,我的确有过一些特别棒的绘画老师,不过,最终我的所学大都来自于实践。现在看来,我的早期绘画都有点令人尴尬,我发表的那些插图也是。不过,当时的我已经尽力了。现在的我也是,而且我可以自得地宣布,我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

《万物运转的秘密》,[美]大卫·麦考利 著,赵耀康 韦坤华 译,小猛犸童书 出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11月
新京报小童书:似乎从童年起,你就对观察和研究事物的“内部”极其着迷。你也曾说过,一切事物在观察和理解的过程中都会变得有趣。也有评论者指出,你的科普图画书一直在力图揭示被隐藏的技术和被遮蔽的内在机制。展示世界内在的真相是你的创作初衷吗?你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对创作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大卫·麦考利: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诞,不过我觉得我成年后的选择大都源于被玩耍填得满满的童年:不下雨的日子,我就会出门,去山脚下的树林里展开我的想象力。那儿有一排排典型的英国工业风砖房,其中一座就是我的家。我会探索无数路径,时而骑着想象中的骏马飞驰,时而停下来观察小溪和池塘,以及某些季节栖息其中的青蛙种群。我会收集有趣的石头,偶尔还有老鼠骨架,或者找到一个视野绝佳的藏身之处。我一连几个小时“无所事事”,却收获了许许多多观察的乐趣。

《万物运转的秘密》内文图。
下雨的日子,我会找出多余的硬纸板——如果没有硬纸板,我会用纸代替,然后制作一些简单的模型,我可以让它们真正动起来。我做过一架电梯(附带一个折叠门),它可以在一个大盒子里上下运行——这要归功于我妈妈缝纫时留下的线头。如果线绳充裕,我还会制作缆车,它在起居室的地板和窗帘杆之间来回运送我的塑料士兵。我最具野心的一组模型包含一个铁路信号箱、一条用打包胶带做成的铁轨和一个信号灯。我的挑战是通过拉动一条线来控制信号灯的升降,这条线压在一段轨道下面,连接着信号箱。我觉得我从没能让它们真正运转过,但我一直没有忘记尝试。我记得那时候我九岁。
新京报小童书:你是如何走上了图画书创作之路的呢?你在大学期间学习了建筑学,但毕业后并没有选择成为建筑师,反而从事了一段时间其他工作和研究。然而,你的第一部作品《大教堂》却是一部建筑学科普图画书。这让我想到,一位艺术家总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将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创作。创作这部建筑学图画书的念头是突然出现在你头脑中,还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呢?你是如何开始尝试创作的,又如何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在处女作之中呢?
大卫·麦考利:在大学里,我本该被培养成建筑师,不过修业未半,我就意识到这不是我想奉献终生的事业。我喜欢解决问题,喜欢制作模型和创作大量草图的设计过程,但当上述步骤结束,我发现我并不想盖房子。毕业后,我在一所公立学校教了一年艺术课,我的学生是十二三岁的孩子,我对此也不太擅长。不过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我人生中可以和创作图书并驾齐驱的另一个爱好——教学。我还开始寻找自由广告插画师的工作,而这又为我带来了一些绘制书籍插图的机会。不久后,我便尝试自己写故事,或者让朋友帮我写一些故事,而我为它们配上插图。在从建筑系毕业三年后,我开始创作第一本书,并在这条路上勇往直前。

《大教堂:为谁而建?》,[美]大卫·麦考利 著,柳漾 译,耕林童书馆 出品,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11月
从创作《大教堂》开始,我的目标便是让看似复杂的事物变得通俗易懂,从而帮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力都超乎自己的想象。大教堂如此宏伟,往往是令人震撼的人造景观。我们走出教堂时心潮澎湃,但又对建造它的工艺感到迷惑。我希望通过视觉化的故事来讲述一步又一步的建造过程,从而向读者展现,那些奇妙的建筑就是由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借助简单又巧妙的木制脚手架,一层一层地累积石块,并建造而成。信仰驱使他们去攀登令人目眩的高度,而常识才是他们得以抵达的原因。
搞清如何最好地呈现信息至关重要。例如,不要一遍又一遍地使用雷同的插画,要调整视点,从技术图纸到透视图的运用不拘一格,用劳动者的特写连续展示一步接一步的工作流程,诸如此类。这不是魔法,这只是常识。
这就是我学习的方式,我通过接连提出一个个问题来分解事物,直到我有能力“重建”我的主题——无论是建筑、自然,抑或我用速写本捕捉的想象,并最终将其展现在完成的画面中。我画速写是为了帮助自己研究正在观察的对象,如果我什么也画不出来,就意味着我对它并不理解。更多的探究是必不可少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不过我知道我最终会达成目标。
看完后读者产生的好奇越多,
一本科普书就越成功
新京报小童书:从1973年你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你在图画书中探索过建筑结构、交通工具的构造、科学原理、生物起源、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你是如何涉猎如此广泛的题材和知识的呢?是在平时就会收集各种资料,并由此获得新书的创作灵感?还是先确定了创作题材,再去收集信息呢?你是如何将庞杂的信息和知识分门别类地归纳整理,再将它们妥帖地嵌入创作之中呢?
大卫·麦考利:答案是“业余时间”。这怎么讲呢?我总是在观察事物,一旦我开始创作一本新书,我就会全天候想着它,比如,睡觉的时候、遛狗的时候、吃巧克力的时候、修理出毛病的东西的时候。只要活着,你就有时间去思考,去质疑,去挖掘想象。我没法假设自己不以这种方式生活。
新京报小童书:你如何化繁为简,将复杂和艰深的知识转化为能够被小读者轻松接受的作品呢?你创作的画面往往极其美丽并精确,还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大卫·麦考利:我喜欢细节,那些不起眼的东西往往推动了大大小小的事物的运转:齿轮的转动、杠杆和弹簧的使用,等等。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而且我相信如果自己画得足够仔细,这种热情可能会“感染”部分读者。我的目标从来不是亮出全部的答案,而是激发好奇心,进而提出问题以寻求更深入的理解。这并不容易,因为一个问题总会引出另一个问题。
我知道的唯一可以说出“停下”的理由,是某个人给出了截稿日期。图书出版合同在这方面很有用,不过我经常超过最初签订的日期,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知道得不够多,不足以看起来像某个领域的专家。也许,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智力和潜在的好奇心。你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在第一次阅读时就全盘理解,因此,你的文字和图画必须足够好、足够完整,以激励更多次的阅读。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报纸和杂志会被扔掉,可书不会。

《穿越时间的船舶》,[美] 大卫·麦考利 著,李天蛟 译,麦克米伦世纪童书 出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年10月
新京报小童书:你的创作跨越了两个时代——《大教堂》中的手绘建筑图令人极其震撼,不过现如今,图画书的创作越来越依赖电脑。你是如何适应新的创作潮流和工具的呢?你认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图画书的审美差异大吗?你是如何协调这种差异性的呢?
大卫·麦考利: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接纳”计算机成为工作流程中的一部分,不过现在它是我的武器库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它永远不能取代我的其他工具,铅笔、自来水笔、纸。我依然把许许多多的草图画在速写本里,或者干脆画在一页页描图纸上,好在我现在可以扫描它们,然后大加改造,而不必一张张地重画。我可以改变比例,用一些元素组合成更大的图像,我颜色,如果效果不好,我还可以将颜色一键删除。电脑给我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我总记不得我把正在进行中的那些文件存在哪儿了。那么多的文件夹、文件和图标。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把文件打印出来,钉到墙上。只有这样,我才感到一切又在掌握之中了。
作为一种信息载体,计算机作用非凡,然而,如果我想理解我在屏幕上看到或读到的东西,我还是必须先把它们画在纸上,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个步骤。要想把一切印入心底,这一步必不可少。

《穿越时间的船舶》内文图。
新京报小童书:在中国,很多小读者因为你的科普图画书成为你的粉丝,也有不少读者非常喜爱你的虚构故事。请问你是如何平衡虚构和非虚构的创作呢?有自己格外钟爱的题材吗?
大卫·麦考利:这两类书我都喜欢,我希望我的创作尽可能有趣、实用,而且富有娱乐性。我特别喜欢直观地阐释事物,不管我是否参与了文本的撰写。真正的挑战来自于选择我知之甚少的主题。这意味着我必须化身为那个学科的入门学徒,直到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用自己的方式来向别人阐释这个学科。这也许会让一本书的创作经年累月,但我得到的最终回报不仅是一本新书,更是我对原本认为理所应当、视若无睹的事物有了更深的理解。
新京报小童书:你的最新创作计划是什么呢?还会继续创作《黑与白》这类具有开创性和颠覆性的故事吗?
大卫·麦考利:我眼下正进行的工作是一本关于地球如何运转的书,我的进度已经比原计划落后了一年。到目前为止,我学到了很多和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有关的新知识:天气、云、水、树木,当然还有气候变化。但我的所学还不足以实现转化。我会达成目标的,但过程并不容易。
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现在太多了,我很为自己的这一本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开发一套个人化的方法来阐释这一主题,而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我从一开始就要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所以这就是我的情况,我仍旧在提出问题,并试图找出哪些问题最为重要。如果要完成这本书,我就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囊括其中。这和以往一样,令人沮丧,但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挑战,我们总是要去面对。它会变得容易吗?不。
新京报小童书:目前中国的原创科普图画书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作品同质化和程式化的问题都较为突出。请问对于如何在创作时打开思路、做出更有个性和价值的原创作品,你能否给出一些建议?
大卫·麦考利:你把最难的问题留到了最后。我认为图画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激发好奇心,它们不需要给出答案,但必须提出问题。在我看来,读者读完一本书后产生的疑问越多,这本书就越成功。通过好奇心,我们与环绕自己的世界在各个层面上建立了联系,无论是表象还是细节,我们都会从中发现乐趣,甚至就连我们从不认为自己会感兴趣的事物也一样。如果我们倾注自己的注意力,哪怕短暂的一刻,就会发现世上没有无趣的东西。
要创造一本有价值、震撼人心的书,需要运用想象力,因为有许多条迥异的道路通往同一个主题。不过,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决心、耐心、关怀和人情味——这可以通过一个小幽默、一个大惊喜,甚至一次短暂的混乱(它会被某种有意义的抉择战胜)来展现。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投机取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不是心怀真正的热忱,就找不到通向非凡成功的道路。
(新京报 采写/刘丹亭 王铭博)
水晶球APP
高手云集的股票社区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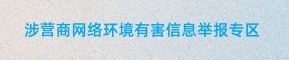

 公安备案号 51010802001128号
公安备案号 510108020011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