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股民的愿望:在布拉格有张床
雷立刚
 / 2017-01-10 18:40 发布
/ 2017-01-10 18:40 发布在布拉格有张床
—— 一个股民的小小愿望
原创:雷立刚
▉
生活在别处,这永远是一件浪漫而感伤的事情,如果是在布拉格,则尤其如此。我没有去过布拉格,但我爱上了这座未曾谋面的城市:爱上了布拉格之春,爱上了弥漫于这城市的淡淡地忧伤着的空气,如果可能,我还打算爱上这里的一间拥有碎花窗帘的房间,但是,显然这太奢侈了,能有一张床就已足够,这张床必当有着洁白的床单,必当有着一睡就可以陷下去的柔软的垫子,必当有着散发着太阳味道的干燥的褥子,必当有着高高的枕头,最好,枕头旁边,能随意地摆放着几个异国的水果,既可以让我懒懒地伸手就够得着,咬一口,满嘴芬芳,又可以作为视觉和嗅觉的调剂品,使我的床充满生命。
于是,我开始不断猜测,布拉格出产什么样的水果呢?最好能有番石榴,因为我莫名其妙地喜欢“番石榴飘香”这个词语组合。但是,我担心它或许只产于南美,担心我的布拉格没有。我在这种担心的驱使下,开始阅读曾居住于布拉格的写作者的文字,因为我知道我将是他们隔代的邻居,他们旧日的生活将在我的今天重演。始料不及,这些阅读令我忧伤起来,我以前不知道生命可以如此脆弱,它不能承受过重或者过轻的东西,我以前也不知道,文字可以将一种疾病传染,这个疾病叫自闭症。
■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些句子:
那些透明玻璃球里的彩色夹心那些自闭症的人
我们的,时代的疾病
这个时代太热烈了,他们说
只有寂静岭里才有安宁
……
有时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或许是双重的,一方面,知识分子陷入了普遍的自闭,另一方面,社会主流陷入了普遍的媚俗。“反对媚俗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无法言说中藏有严酷的真理,振振有辞中含有美丽的谎言”(引自韩少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前言),我个人以为,这是人生的无奈,也是人类史的无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共同组合成人类的生命,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奈的,那么人类的生命也是无奈的。
在当年的布拉格,莎宾娜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GC主义,我是反对媚俗。”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一章第一节,昆德拉说,“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这些语句触目惊心,与我们的今天何其类似。今天,一方面,所谓精英,正在普遍性地接受“资本决定发言权和表决权”的理念。坦率地说,我不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但我讨厌这种绝对的倾向性,就如我反对国家机器的绝对化宣传一样,我同样反对民间知识界那种占压倒优势对西方的迎合,我讨厌所谓“民Z人士”,也不认同所谓“自由斗士”,我并不认为敢于跟政府对着干就是勇敢,我相信真正的勇敢在于面对人人心中皆有的黑暗。
在这个黄昏,在远离布拉格的中国西部内陆城市成都的边缘,在我栖居的荒凉的房间,我记录下这些忧虑。
■说起死亡,就不得不考虑生命,说起生命,就不得不考虑人生的问题。尽管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我们每个人,包括昆德拉自己,依然无法回避思考,这是生命的悖论,同样无可奈何。
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的扉页上写着:“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与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
这正是最让人悲哀的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正在参与这荒唐的人生。我们象蚂蚁啃骨头一样为利益操劳,但那些骨头除了延续我们的生命究竟还有什么其他意义?
我很喜欢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曾经看过这么一部记录片,关于美洲一种美丽的蝴蝶。它们一出生,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破卵而出剩下的卵膜,然后立即一刻不停地吃树叶,连排泄时也在吃着,一分一秒也不浪费。很快,他们就变成了茧,七天后,和上帝造物花同样的时间(当然,上帝休息了一天),它们化蛹为蝶。然后一刻不停地由美洲北部飞到南部。因为上帝规定它们必须在南部交尾。而此时,天气总是开始变冷,空气寒流自北而下,它们必须和寒流赛跑,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冻死。那些运气好的蝴蝶终于非到了南方,自由地交配,我很好奇,它们的交配有什么样的快感?有几分钟或几秒钟的快感?蝴蝶中有没有性无能分子(那它这一趟万里长征岂非白费功夫)?从它们整个生命里程看,它们的觅食和远征都只要一个目的,那就是交配,而它们交配的目的其实在于——延续它们的种群。此刻,它们的个体完全是延续种群的一个机器,个体的生命或自由其实是多么荒诞。
由于它们生命的短暂,我们人类得以在很短的时间里目睹了它们数代蝴蝶的历程。我们发现它们每一代蝴蝶其实都是类似的,于是我们发现了它们个体生命的荒诞与微小。但对于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却在意的很,但是,如果有另外一种生物,它的生命是人类的数百数千倍甚至数万倍的话,它目睹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在它的眼里,或许我们每一代人其实是多么类似,尽管所谓社会制度在不断变化,可人心中的那些欲望究竟有多大区别?我们今天的痛苦感觉或许五百年前的一个书生完全经历过,我们今天的愉快感觉或许与五千年的一个祖先偶尔捕到一条大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自以为自己很贵重,其实我们也只是蝴蝶般的一个机器,延续种群的机器。
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思考下去,更能发现造物主的极度的残酷阴毒。你看,它既要那些蝴蝶为交配而不懈努力,又偏偏不让那些蝴蝶轻松地交配,它非让它们跑几千里,到南方才能交配,还要适时地让寒流袭击而来,象追击流寇一样,让蝴蝶们惊恐不安。太残忍了,它为何不让这些蝴蝶就地交配呢?再看造物主对我们人类的手段,何尝比对这些蝴蝶温柔半分?它让人类互相倾轧,将人类分成金字塔塔般的阶层,给每一个人一定的社会分工,使“别人就是我的地狱”,利用别人来压迫别人。让每一个人企图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向上向上再向上,以期获得相对优势的社会分工。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从小是一个逆反的人,无数的教训,使我懂得了一些关于逆反的秘密:适度的逆反可以使你获得一些捷径,因为永远的人云亦云不会令你与众不同,而不与众不同,就不可能得到社会额外的份额。
但是,当你的逆反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你就将开始付出惨重代价了。这个限度就是不能与大多数人为敌,也就是不能与上帝制造的规则为敌。上帝很狡猾,它制订的规则说到底,其实就是“如何有利于人类物种繁衍就如何干”,但是它给这些规则披上了美丽的外衣,美其名曰:道德。道德是可以杀人的,而且不见血。
我还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关于道德的秘密。就象那些蝴蝶一样,你压迫其他蝴蝶,你不按游戏规则飞翔,其实都是上帝允许的,因为这样有利于物种的繁衍。但是,你若不按上帝的要求到南方去交配,那你就只有冻死的份了。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你吃人,没关系,因为剩下的没被吃的人拥有更有利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繁衍下去的良好生存能力基因。但是,你如果不按上帝的要求遵循金字塔规则,不参与到社会分工中来,你就等于慢性自杀。因为你违背了这个物种的潜在要求,你明明是反上帝,但上帝懂得怎么修理你,他不用自己动手,他借刀杀人,他给你的罪名永远不会是“反上帝”,而是一个更具道德威慑力的罪名——“反人类”。
上帝是我所知道的最可耻的东西。如果我的灵魂可以不灭,如果我对上帝的仇恨可以在这宇宙间不断轮回,那么,我将用无限的时间来诅咒这可耻的叫做上帝,或者叫做造物主,或者叫做神,或者叫做命运的东西。我很你,恨你的嚣张,恨你的一切尽在掌握。这是与生俱来的仇恨。
■除了极少数成功的股民之外,这个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股民,其实是被动或主动放弃了社会分工、驱逐自己于社会规定程序之外的一群人,我亦是其中一员。股市貌似门槛很低,却又是最为艰难的一条道路。中国股市总是牛短熊长,一旦没能抓稳那短暂的牛市机遇,多数股民的生活将会变得一塌糊涂,不必质疑,这绝对只是迟早的问题。很多事情是我们股民踏上这条道路之初,根本无法料到的,我们本以为失去的仅仅是社会的面具,但最终会发觉,失去的还包括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些根本可能包括:住房,爱情,婚姻,退休金,医疗保障,等等。
今天清晨,天刚刚要亮的时候,我顺着东风渠,沿河而行。水面仿佛象牙白的带子,那么近,如同昨天的镜子,却又那么远,如同天上的银河。我亲眼目睹着路灯象闭上眼睛般熄灭,而天边的云破处,太阳一如既往地升起。我发现,不管生命本质上是如何虚无,但作为感受生命的个体,在这感受的过程中,其实不时有着温馨。我们不能永远象彼得·潘一样当一个孩子,尽管这可能是每一个存在于生活重压下成年人内心深处的梦想。我们无可奈何地承担着义务和责任。且行且珍惜,这可能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
在这个清晨,我回忆起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我想起他对于个体苦痛的一些描述,他说,“……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那一刻,我心底泛起如同巨大湖面里细小涟漪般的忧伤——因为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将背弃这个我曾经热爱的诗人和他们那个时代的歌者。即便人类所有的忧伤和喜悦都如此类似,我依然有责任将它们重新品尝,为了将来可能某一天,我能到布拉格旅行一趟,哪怕仅仅只是某一夜的某一张床。
这个早晨因此而由最初的忧伤变得快乐起来,成为“我快乐的早晨”,即便所有人在大街上集合仅仅是为了庆祝某些伟人的生日什么的,即便人类最有创造性的精神总是被迫沉默,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快乐。正如克里玛所说,“生活常常在两种苦难两重虚无两种绝望之间给人们提供一种选择,而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更容易忍受和更有吸引力的一种。”
在这个早晨,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诅咒制造生命的上帝,但我们不可以诅咒生命本身。
2017,1,10.雷立刚于凤凰城
水晶球APP
高手云集的股票社区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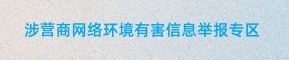

 公安备案号 51010802001128号
公安备案号 510108020011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