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中国谈:从“仁孝治天下”到“科技强国”
薛洪言
 / 2020-01-29 11:06 发布
/ 2020-01-29 11:06 发布关于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有本经典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1920年代。在那个大变局时代,中西文化激荡冲突。国弱则势弱,西方文化有科技船炮做支撑,代表着进步,一贯而入,所向披靡;中国文化则像古董,看着好玩,在国际竞争中全不实用,步步后退,几乎要被连根拔起。
经历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后,有识之士愈发感到要加速引入西方科技与制度,可东西文化在根本上不相容,导致很多西方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于是便有了“假如采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东方化不可”的呼声。
可是,究竟何为东方化?何为西方化?二者又有何本质差异?不对这些问题做个彻底探究,要改造文化谈何容易。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梁漱溟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西文化之根本差异 对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梁先生事后多有悔恼之语,认为书中观点多有偏颇错误之处,并一度要求出版社停印。不过,对书中核心论点,梁先生又极其自信,自言“百世以俟,不易吾言”,并补充道:
“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欠,而大端已立,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东西文化,梁漱溟认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中国的很多事物,都是师徒心传的手艺(特指封建时代的中国,下同,作者注),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所以“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而西方则靠科学,“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把一切分门别类,衍生出细分的学科和学问。
以看病为例,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中医的高手,水平全在开单用药,病灶病因与药品温凉,凭主观判断,十个医生十个药方,可以十分悬殊。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求新,事事日新月异;中国文化尚古,几千年不见进步。因为“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
在中国,“既无学术可以准据,所以遇到问题只好取决自己那一时现于心上的见解罢了。从寻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所以,中国的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案子也审得,财政也理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一件事;在西方,则决然不同。这就显出了19世纪之前中西方在社会治理上的区别:中国尚人治,西方尚法治。
人治之下,自然有尊卑高下,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别,且“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国人在国家层面是皇帝的臣民,在亲子之间是父母的儿女,是父母所有的东西。
“他父亲如果打死他、卖掉他都是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夫妇之间做妻子的又是她丈夫所属有的东西,打她、饿她、卖掉她,很不算事”。 此便是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西方法治之下,人人“治人”,人人也“治于人”,去尊卑而得平等。“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于是便有了“个性的伸展”。个性伸展必然辅以社会组织发达,否则各行其是,没有协调,是走不通的。个性与社会性,互为扶持,缺一不可,所以西方的社团群体也很发达。
因社会性发达,西方注重社会公德,讲究公私分明;中国则讲五伦私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可以枉顾法律,公私不分明。
文化差异因何而生? 上面略讲中西文化差异,但差异因何而生呢?同时代的学者多讲“地理决定论”,即:
“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勤劳为活,所以要发明自然科学,征服自然;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卒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梁漱溟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迫促的境遇不是适于产生科学的缘法,倒要从容一点才行,单为用而不含求知的意思,其结果只能产生“手艺”“技术”而不能产生“科学”。所以,西方文化里对科学的推崇,与“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无根本关系。
梁先生认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根源于面对生活中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
面对问题时,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个路径:
(1)向前面要求;
(2)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3)转身向后去要求。
对应来看,西方文化,是以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征服自然的路子;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与自然融合的路子;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出世的路子。
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西方无疑走的是第三条路,寻求在天国得救,但文艺复兴重新让西方走向第一条路。关于这种转变,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曾评论道:
“文运复兴的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的态度以后,一向从那方面走——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愈演愈大,酿成十六世纪的‘大改革’,十八世纪的‘大光明’,十九世纪的‘科学时代’,二十世纪的‘平民主义’”。 《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作者蒋百里先生也曾评论道,“人也者,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足可见,摆脱了教会的辖制,西方文化才终于走上了“向前要求”之路,开辟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时代。
就中国而言,在走第二条路,如梁先生所言:
“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易》。讲《易经》的许多家的说法原也各有不同,无论如何不同,却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他们虽然不一定像这样说词,而他们心目中的意思确是如此,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 在这种文化思想下,“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他持这种态度,当然不能有什么征服自然的魄力……他持这种态度,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路”。
至于印度,则是第三条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出世)的”。

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 由于西方国势强盛,所以一般人看来,西方文化的第一条路是高级的,而印度第三条路则是落后的。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在他看来: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1920年代,作者注)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 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并非落后于西方文化,只是提前跳过了第一阶段罢了。如印度文化,因先天条件不同而提前走上第三条路:
“大约印度当时因天然赐予之厚,生活差不多不成问题,他们享有温热的天气,沃腴的土地,丰富的雨量,果树满山,谷类遍地,不要怎样征服自然才能取得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且天气过热也不宜于操作;因此饱足之余,就要来问那较高的问题了。” 当然,印度文化提前走上第三条路,与其种姓制度也有关系。“本来印度人的那种特别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非可遍及于平民,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生计有安顿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
就中西文化而言,梁先生也是认定为讲究“调和”的中国文化更胜一些。在他看来,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因为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正所谓:
“无论什么人——自低等至高等地位——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小心提防失败、贫困、地位低降,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时时刻刻算帐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而统驭着自己,去走所计算得那条路。他不敢高狂,不敢狷介,不敢慷慨多情乃并不敢恋爱;总之不敢凭着直觉而动。……其苦恼还不在抑制统御,而在抑制统御之后所生烦闷、倦疲、人生空虚之感。这才是大苦恼,人当此际简直会要溃裂横决!断不会容他长久如此。” 所以,尽管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第一阶段是必经阶段,但终归,人类社会要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进入精神不安宁时代。这个时候,人类不再能承受“以对物的态度对人”,也不能容忍“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的状态,主流的文化模式不得不变。
于是,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
跳级是行不通的 但是,复兴是未来的事,当下阶段却要补课,即提倡奋往向前的风气,着力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没有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一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 我们处于第一个问题之下的世界(物质不满足时代),却直接走上第二条路(精神层面),一旦与世界接轨,必然是节节失败。
站在1920年代的时间节点,梁先生得出结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科学精神的发展、追求个性之伸展,仍是复兴传统文化之前所必经之阶段。
以上,仅仅粗略概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要点,更多精彩观点,建议大家去看看原书。本书虽成于1920年代,但文化演变何其缓慢,时至今日,书中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环境与社会,仍有诸多启发裨益。
经典,向来是不过时的。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处在补课的第一阶段——追求创新、奋勇向前。这个阶段侧重于物质进步,难免对精神层面照看不足,但世间本就没有两全之事,跨过这个阶段,才能进入下个阶段。
就每个人而言,倒不妨多接触传统文化,丰富精神生活,与注重物质进步的大环境做个调和。
本文由“洪言微语”原创,作者系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薛洪言
参考资料: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8.
水晶球APP
高手云集的股票社区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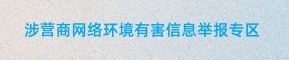

 公安备案号 51010802001128号
公安备案号 510108020011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