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中国的命运转折
星图金融研究院 / 2020-01-26 15:15 发布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游子春节返乡的一段段旅程,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春运。
2020年春运自1月10日起开启,国家发改委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将达到30亿人次,若以每人往返两人次进行简单估算,相当于14亿中国人每个人都参与了春运。有人也因此调侃称——中国的春运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迁徙。
乡土中国的变迁
春运的背后,是人们对乡愁的寄托,不论离家多久、工作多忙,过年都要回家和家人团聚。但从经济角度看,春运的背后,是这几十年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巨变,这些变化中,最明显的就是人们离开家乡,到异地工作生活。
在此,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人们形容中华民族,“安土重迁”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土地自古以来是百姓的命根。费孝通先生在其论文集《乡土中国》中总结道,“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的。”
为什么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深厚?
因为几千年来,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种地,很少离土离乡,人口的流动性极低。
各地种植的粮食并无什么不同,各个乡村之间也没必要互相交易。进而以交流和交易为基础的工商业没有得到持续发展。
不过,工商业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的自然产业形态。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中国自周朝便初步形成了商业,并在中国的汉、唐、宋三朝都出现过繁荣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
但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商人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对官府的权力是很大的威胁。因而,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向乐于打击、限制商业和商人,并用官方的经营去代替,但官营的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史就出现了这样的死循环:
新王朝建立,减轻赋税,放松管制,商品经济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出现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大商人和富农增多,朝廷害怕,往往要强制推行官营工商制度,把经济管起来。管得太紧,经济不景气,财政收入就紧张,国家只好加税,百姓负担太重,发动起义,推翻王朝,从头再来。
既然工商业受抑制,绝大多数人靠伺候庄稼为生,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乡土之气由此慢慢形成。
千百年后,新中国成立,公有化经济制度确立,土地归集体所有。彼时国家重点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此,农业要补贴工业,为工业发展创造低成本的有利条件,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由此形成。
也是在50年代,国家确立了与土地直接关联的户籍制度。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并第一次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农业补贴工业,农民也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及其工业得到了发展,但农村经济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直到1978年11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在分田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手印,从此“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农村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且这些剩余劳动力大多是青年人。这是因为在生产效率提高后,大面积的土地种植经营只需少数人就能完成,大量年轻人无事可干。
当时,这些人可以去城市工作吗?不可以,城市的大门还没有向这些年轻人打开。
那该怎么办?乡镇企业这个新事物应运而生。大量年轻人开始离土不离乡,即离开农业去从事工商业;进厂不进城,进入当地的乡镇企业工作,但并未进入城市。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权宜之计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资源,促进乡村经济繁荣,改变单一的乡村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改善了工业布局、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到200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比1978年的9.23%提高了10个百分点。
由此,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中国农民开始了千百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土离乡。
“农民工”也开始了城市迁徙之旅,为城市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正式开启。截至2019年,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74亿人。

农民工进城的背后,是城乡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到2015年,城市收入约为农村收入的3倍。
让我们来算一笔账,保守估计,一个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每个月收入为3000元,每年的收入近4万元。截至2013年,中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平均每个农民的耕地面积为3.67亩,若种植主粮,即使不算种子、农机和灾害损失等成本,每年的收入在2000×3.67=7340元左右,有一小部分土地种植了附加值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好的年景可以获得3万多元的收入,也远远低于城市务工收入。
城市的收入更高,前途更光明,是农村人口离开故乡、进入城市的主要原因。

从离土离乡到离土回乡
从上面农民工增长的图示中,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农民工数量,尤其是离土离乡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的趋势在减缓。
表面上来看,这与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空间明显矛盾: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0%左右,日本的城市化率甚至超过了90%。

若以发达国家为参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走完,提升空间依然巨大。但为何农民进城的增速变慢了?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滞缓。2016年,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紧紧围绕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完善财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策。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督察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落实情况的通知》。到了2018年,国家发改委又发了一遍督查通知,方案落实的速度缓慢。
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滞缓,也影响了乡村的改革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始终拥有在家乡的土地,包括耕地和宅基地,这些土地都是无偿划拨的。但近些年,这些土地出现了闲置现象。很多进城的农民工宁愿荒着家里的土地,也不愿意转让给别人,因为一旦他们年老或生病,无法继续在城市打工时,他们需要回到家乡的土地上谋生。
这造成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农业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的产业,大规模农场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土地分割的小规模种植经济。但土地被闲置、流转不起来,土地的整合就受到了阻碍,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场。
中国农业没有规模经济性,产品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卖不出去的农产品成了库存。但市场又存在大量粮食需求缺口,只能依靠大量进口去填补。
反观美国,美国人口约3.3亿,其中农业人口约2%,仅600多万人,但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也是全球农产品最大出口国。
乡愁情归何处?
行文至此,我想让大家回答下面两个问题:
中国的脱贫问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还是依靠政府补贴?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依靠城市,还是要依靠农村?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就是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继续推动农民进城,给予他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让城市成为他们新的故乡。
农民有了新故乡,原来的乡村怎么办?我想这也不用担心。
总体而言,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和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地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达到类似均衡状态下,大致会呈现这样一种景象:各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可能会相差巨大,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产出是互相接近的。这也将是未来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平衡发展的方向。
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下面的美国经济的地理分布图。这幅图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在其著作《大国大城》中绘制的。图中,蓝色区域和红色区域各占美国GDP的一半。可以发现,美国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五大湖以及南部个别地区,而面积广大的其他地区经济规模都较小。

总量分布的极其分化,并不妨碍人均层面的平衡。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参见下图)。

从城市化角度看,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将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下图中,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城市化率往往也越高。若按照每年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还要20年。假定中国总人口不变,要达到美日韩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的人口将增加约2.8亿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因此,谁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的时间窗口至少还有20年。

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依然存在一些限制。但反过来看,中国蕴藏着巨大的“结构性”劳动资源的潜力。若以上所述的人口流动限制得以放开,可以想象,能够释放出非常大规模的潜在劳动要素能量。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的大门在慢慢打开,2019年底,国家取消和放宽了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的落户限制。未来,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的落户制度也将得到改善。
其实,从我们身边就可以发现,一部分在城市奋斗成功的外来人口已经完成了举家迁徙,每到春节,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回到原来的家乡,而是留在了城里过年。城市已经成了他们新的故乡。
故乡,这一千百年来让无数游子魂牵梦萦的词汇,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被重新诠释。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
水晶球APP
高手云集的股票社区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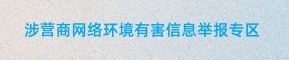

 公安备案号 51010802001128号
公安备案号 51010802001128号